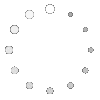|
| 第8版:绿洲 |  |
 |
| 版面导航 |
| · 最后一张执勤照 |
| · 父亲和两只小鸡仔 |
| · 我们曾那么郑重道过别 |
|
|
| 【字号 大 中 小】 | 返回主页 |
| 我们曾那么郑重道过别 |
| ■徐卉婷 时至清明,最忆亲人。 这些年,若要说有哪个瞬间,是在脑海中始终挥之不去的,一定是那一次的回头,那是爷爷被推进ICU病房前的一次回头,也是他此生留给我的最后一次回头。 15年前那个秋天的上午,一切都发生得很突然。爷爷在住院数日后,床头监测血氧饱和度仪器上的数字一直掉,医生说要进ICU了,一屋子的家人无所适从,医生说要进,那必须进。接下来的一分钟时间里,医生、护士、护工熟练地摘掉了爷爷脸上的氧气罩,把他抬上了推床,我愣愣地站在一旁目睹这一切的发生,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。 爷爷可能实在没力气了,没有说一句话,也没有任何反抗的动作,直到推床启动,朝病房门口滑去,爷爷突然艰难地侧着头,转过来看着我,似有什么话想说。我跑着追上去两步,他没有开口,只是定定地看着我,推车拐弯,爷爷从侧着头变成仰起头,脖子抻到极限了,眼睛依旧努力看着我的方向,直到被推出房间,一堵墙把我们彻底阻隔。 我没有像电视剧中那样,追着推床一路跑,我以为爷爷还会回来的。我也不明白爷爷为什么要这样看着我,他大概想说什么,但我觉得不着急,等他从ICU出来了,我们可以慢慢说。可不知道为什么,心却揪起来地疼,看到他那么艰难地回头,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掉。多年后才知道,进了ICU的人,是很难再出来的。 父亲一直守在ICU门口,到了半夜,医生来征求家属意见,父亲知道爷爷不喜欢医院,决定趁他还有最后一口气把他接回家。车子从硖石开往袁花途中路过爷爷的老家谈桥,父亲告诉爷爷:到家了。爷爷的眼角流出两行热泪,然后就陷入深度昏迷,直到身子慢慢变凉。这些是后来父亲告诉我的,父亲没有半夜把我叫起来,第二天等我接到电话赶回袁花,爷爷的脸上已被盖着一块白布。 我猛然意识到,这个回头,是爷爷留给我的最后记忆。 10多年来,我一遍遍回想着这短短的几十秒,明明只有几十秒,我却想了10多年。他头顶那蓬稀稀拉拉、白透了的头发,他脸上每一道褶子和因为喘不过气微张着的嘴,他浑浊的、努力睁开着的双眼,他粗粝瘦削的、抓着床沿的双手,还有他僵直着、艰难变化着角度的脖子,就像电影里慢放的镜头,一闭眼,每一帧都烙在眼前。 爷爷一生硬朗,很少回头。青年时在战场上被子弹洞穿了大腿,落下终身残疾,伤口始终没有愈合,日夜流着脓血,他每天都要把纱布生生从伤口上扯下来,用双氧水给伤口消毒后再重新包扎,他从不吭声;退伍回来后成为一名理发师,靠着一条腿站立给人理发,客人一位接一位地坐下,他一站就是一整天,他从不怕累;后来理发店关闭了,为了补贴家用,他摆起了卖竹器的小摊,把拐杖往推车上一挂,风雨无阻地出摊,他从不嫌苦。 可就是这样一位不怕痛、不怕累、不怕苦,一生都咬着牙向前走的人,在那一刻却回头了。 10多年过去,在经历了更多的生死别离后,我终于明白,那一刻,爷爷是在与我们告别,以他的性格,他不会惧怕被推进ICU经历各种复苏按压、抢救插管,他不会害怕即将来临的死亡以及分别。只是,他知道自己已经出不来了,所以他想最后再看看,看看他最爱的亲人、看看这个世界,他知道,这一眼之后,便是永别。 那一刻,在我满心以为爷爷还会安然回来时,他却已经做好了离别的准备,他在推床上,目送我的身影消失在那堵墙的背后,他用眼神告诉我,不必追,不必追。 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为没有见到爷爷最后一面而耿耿于怀,直到我理解了那一回头后才豁然开朗:原来我们曾那么郑重地道过别了。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