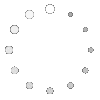|
| 第8版:绿洲 |  |
 |
| 版面导航 |
| · 游向岸边 |
| · 愿你如雅鲁藏布江般奔涌向前 |
|
|
| 【字号 大 中 小】 | 返回主页 |
| 游向岸边 |
| ■徐卉婷
我的童年时期,有件颇以为傲的事:6岁就学会了游泳。我没有问过父亲,为什么要这么早教我学游泳。我想即便问了,他也未必能答上来。 总之,那年我在袁花镇西边一个叫“陈家兜”的鱼塘里学会了游泳。鱼塘的水很脏,每次从水里上来,手臂和腿上都长了粗粗的“汗毛”,现在想来还觉得汗毛一凛。鱼塘里人很多,父亲需要不断拨开人群,才能清理出一条“泳道”。父亲总是皱着眉,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,若岸上出现一个长得胖点的人,父亲就会朝他喊:喂,你轻点下来!确实,动静一大,鱼塘里的水就会晃出去一些。我也跟着忧心忡忡,生怕鱼塘的水会越来越少。 父亲的自由泳非常标准,潜泳能贯穿整个鱼塘。可是这些技能他统统没有教我。我最终学会的是一种下巴高高抬在水上面,双手上下拨水似狗刨,双腿又蹬又踢的怪异泳姿。不过这种泳姿在当时浑浊不堪的鱼塘里非常实用,可以避免我的眼耳口鼻灌入泥水。但是除了实用之外就真的一无是处了——它既游不出速度,更不美观,看起来非常业余。 对此,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敢怒不敢言。直到多年后,我怎么也教不会自己女儿跳绳,才明白父亲也许是有苦衷的。 20多岁,我工作了。有一年参加单位疗休养,第一次在三亚看到了壮阔的大海。我想大海真好,完全不用担心一个胖子跳下来会把水晃出去。 我一步步往海水深处走去,直到脚尖再也触不到柔软的沙滩,往前一扑,变成了游泳的姿势。 下巴用力抬起,双手拇指并到食指第一关节,手掌呈蜷曲状从上往下拨水,双腿收缩向外向后蹬去。一沾水,沉寂了十多年的肌肉记忆迅速觉醒,身体的每一个关节、每一块肌肉都在坚决执行着父亲当年强调的动作要领。就像一条出生后就被遗弃在岸上的美人鱼,在触水的刹那,本能地摆动起了鱼尾。 我游啊游,一直游到了海滨浴场最外围的警戒线,一直游到身边的伙伴都消失了,一直从海水浅蓝色的地方游到周围全部变成深蓝。 最近,看了余华老师的《一直游到海水变蓝》,他历经生死也只到了海水变绿的地方,不禁哑然:还真印证了那句话,有些事选择比努力更重要。 三亚一战后我对自己的游泳技术信心爆棚,总想着要跟人比一比。所以,在充分接纳自己狗刨式泳姿的基础上,我潜心钻研,保留核心技术,在形式上略作改良,丝滑进阶到标准的蛙泳。然后开始参加游泳比赛,竟然屡有获奖。 获奖容易让人膨胀,导致我对自己的真实水平蒙上了厚厚的滤镜。我甚至觉得:一个在大海中遨游过的人,再回归到泳池这方“静水”,简直就是降维打击。 我的想法引起了“静水”的强烈不满。 前年,我们一家三口来到台州仙居的淡竹乡,我从未见过如此漂亮的石滩和溪水。群山环绕下,它们深一潭、浅一滩地随意分布着。晶莹剔透,涓流潺潺,让人只能想到四个字:人畜无害。 我和女儿迫不及待地找了一处地方下水。我们穿着鞋,没打算走深,可是在溪水覆过脚背的一刻,竟被一股神秘的力量吸引着步步深入,直到一脚踏空——我和女儿溺水了。 刚刚还人畜无害的溪水,此时却不由分说地漫灌进我的眼耳口鼻。一个遨游过大海、驰骋过赛场的人,竟然在阴沟里翻船了! 女儿挂在我的脖子上,她也被这突如其来的“没顶之灾”吓傻了,忘记了自己会游泳这件事,死死地勒着我的脖子,挂在我胸前不撒手。我努力托举着她的屁股想把她顶上去,可是穿着拖鞋的双脚仿佛被束缚住了,根本提不起来。 想喊救命。明明玩桨板的人就在一米开外,可是我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,脖子被溪水狠狠扼住。刚刚还如此散淡随意的溪水,竟然可以在刹那间集结起来,迸发出令人窒息的力量。 放弃求救的念头后,我开始专心自救。可是女儿挂在脖子上,我那进阶后的蛙泳姿势完全施展不出来。这个时候,只有双手往下拨水,我们才能寻得喘息的空间,是时候回归到狗刨式了! 于是,37岁那年,在面临死亡威胁的时候,我决定乖乖回归到6岁那年学会的、除了实用一无是处的狗刨姿势。靠着它,一点一点把自己和女儿推到岸边。 当我最最嫌弃的,下巴高高抬在水面上的泳姿重新出现的时候,我们母女俩获救了,我喜极而泣,无比感谢父亲。 回来后,我重新充值了游泳馆的储值卡,退回到最安全的地方。 余华在历经生死之后游向更远的远方,所以他成了余华。而我在被扼过一次喉咙后,只想游回岸边,所以我只能是我。 我想,父亲在我6岁那年教会我游泳,从来不是为了让我去闯荡、去战胜、去争抢;他只想我平平安安,在每一次遇到风浪的时候,在每一次被命运扼住喉咙的时候,都能顺利脱险,游回岸上。 |